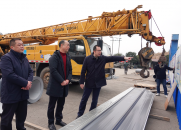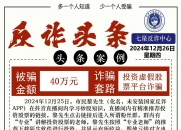|
南宋隐臣唐子超
前言 唐子超(1164——1244年),字希陞,南宋隐臣,民国《全县志》指出他是“宋时宦全州遂卜居于”白宝,清代唐氏族谱记载他是“宋理宗时选登仕藉授中宪大夫以荐举任广南观察使”,所以唐子超是南宋隐臣无疑。他生于江西吉水,年轻时为司马司务,驻豫章南昌府,后奉令征运财赋、皇粮和贡品,因“湘江翻船”和“道州被抢”,遂归隐全州白宝迎马山。唐子超拓荒白宝,开发都庞岭,创建古梧洞,迁建慈恩寺,沟通湘桂官道,缔造了全州最古老、最奇崛的山乡文明。他是全州恩乡的人文始祖,是白宝文明的奠基人和肇创者,白宝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唐子超,比东山早两三百年。
很多写史的人,畅谈全州文明博大,却不知白宝文明奇崛。白宝之于全州,好比高山之于平原,石林立于沃土,风物有异,人文亦深。只有充分了解,才能足够重视。只有登堂入室,才能笼山川于形内,挫历史于笔端。
民国大师辜鸿铭说过:要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关键的问题是它能够塑造怎样的人,怎样的男人和女人。一种文明所塑造的男女大众,才能真正体现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就是这个文明的灵魂。
说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上面怎么少了元代?答案是元代难出人才。蒙元灭宋,满清入关,都是野蛮颠覆文明,落后取代先进,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是华夏民族的最大悲剧。唐宋两朝,官员见皇帝是不用下跪的,元朝入主中原后,把它的奴化体系推向全国,大臣见皇帝,平民见官员,都必须下跪。全州南宋遗民,包括白宝唐氏,自然是以孔孟之道为正统,自觉远离官场,抵制不正之风。而且,元朝直到快灭亡的时候,才开始实行科考制。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寒门难出贵子,像白宝这样的穷乡僻壤,尤其难出人才。
唐子超八百年前就隐居全州,是白宝文明的奠基人和肇创者,是全州恩乡的人文始祖。他的故事见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蕴含着无奈、悲伤与美丽的维度。
学湾塘翻船 过道州被抢
唐子超,字希陞,南宋人,宋隆兴甲申年(1164年)七月初二生于江西吉安吉水,宋淳佑甲辰年(1244年)二月十五卒于广西全州白宝,享年八十一岁。他年轻时为司马司务,驻豫章南昌府,后奉令征运财赋、皇粮和贡品,往返于广南、湘江和临安,因“学湾塘翻船”和“古道州被抢”,遂归隐全州白宝迎马山。
“学湾塘翻船”指的是唐子超押送的皇家船队在湘江倾覆,事故发生在湘江全州段“学湾塘”水域,即今全州文化公园岸边。学湾塘乃湘江曲流,地势低陷,忽然拐弯,暗流汹涌,自古就是水患多发地。南宋年间的一天,唐子超率领一支满载物资的皇家船队,从桂州驶入湘江全州段,行至学湾塘拐弯处时,忽然陷入漩涡。来不及躲避,数船倾覆,唐子超落水,幸得侍卫救护,他才抓住马尾巴奋游上岸,逃过一劫。但财物沉没,多人溺亡,损失惨重。处置沉船事故之后,唐子超自知官做到头了,便拟就奏折,叙己无能,指挥失当,无过他人,如今年老体衰,伤病叠加,恳求就地生养,遥候朝廷降罪。之后,便命令剩下的船只继续前进,回临安复命。所幸“理宗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天朝念他劳苦功高,情有可原,便置而不论,未加追责。
皇船倾覆后,唐子超无数次徘徊在学湾塘,与当地郡守在湘江上游设立危险警示标识,并在龙山上筹建阁楼凉亭,以补地势,镇水患,引瑞气,振文运。“学湾塘”是唐子超的滑铁卢,也是他的伤心之地,人员物资损失惨重,他嘱咐子孙后代记住这个地方。
至于“过道州被抢”,则是发生在翻船之后。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皇船倾覆之后,唐子超又回岭南征集了一批军赋,这次是陆路押送,一路畅通无阻。但在过道州时,前锋粮队遭遇一群饥饿的难民,难民们先是跪倒在地,呼天喊地,哭诉救命,进而挡住去路,把军粮财赋哄抢而光。唐子超体恤民生疾苦,阻止了卫兵对难民的追杀。
隐居迎马山 创建古梧洞
连出两件惊天大事,唐子超必须回临安述职,便率领一干随从策马扬鞭赶往洮阳,计划坐船经洞庭至临安,在到达洮阳一山腰空旷地带时,坐骑突然不走了,无论怎样抽打也不肯前进半步。唐子超无奈,抬头一看,只见山顶挂着大片彩云,一团紫气从东而来,显然是天降祥瑞,地现吉星。唐子超甚为激动,下马环顾四周,察看风水,只见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眼前的景象促使他下定了归隐之心,于是抱着马的脖子说:“畜生唉,你跟着我也造孽了……你不走,我也不走了!”
唐子超下马的地方就叫迎马山,位于今白宝境内,古梧洞之东。迎马山雄壮高峻,气势磅礴,自古有“衔东山,吞城关,一统楚粤风光”之誉。唐子超没有东归,交接公务后,便率领家人于迎马山凤凰洞奠基,“建四十八条栋梁之庄”,“创置户山周围二十五处”,确立了“耕读传家、诗书济世”的家规,以及“居官则清正爱民、在家则忠厚训子、为人当乐善好施”的家训,寄寓了他对山乡子弟的教诲与期望。
迎马山凤凰洞,是唐子超在白宝的第一居所,正在古道旁边。白宝古道主要有两条,全州东门粟家渡过河,经绕山、冲口岭、迎马山至白宝岭分道,一条经楚粤亭、婆婆殿通往零陵,一条经文家庄、文市到达道州。随着拓荒的伸展,唐子超又创建了古梧洞。古梧洞在迎马山西面6里处,地势较低,地形平坦,为群山环绕,至今有22个村庄坐落于此,自古就是恩乡十二都难得的洞天福地。
唐子超以古梧洞为地基,创建四宅分属四子:长子唐志远,字舜卿,宅于桐木岗,居西;次子唐志道,字震卿,宅于莲花村,居南;三子唐志星,字善卿,宅于乔田坊,居西;四子唐志明,字仁卿,宅于白水底,居东。后来,桐木岗和乔田坊连成一片,就统称桐木岗。桐木岗背靠卧虎山,以梧桐树多而得名。莲花村偎依青龙岭,宅边有一池塘,池中有数眼清泉上涌,水中有礁石点缀,所以叫莲花村。白水底村背靠连绵青山,村后有一条溪水倾泻而下,远远望去宛如白练腾空,银河飞流,甚为壮观,故曰白水底。从此,古梧洞开枝散叶,以都庞岭为根据地,以古官道为生命线,青石铺路,十里一亭,代代拓展,力拔山兮破天荒,至清初奉旨入川,子孙后代遍及湘桂川渝,广居五湖四海,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其泽被后世的伟力在全州祖坛实属罕见。
迁建慈恩寺 奠定古文明
一个人,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百般谋划,千回奋斗,都不如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唐子超慈悲为怀,深谙此道,这从他给孩儿们取的名字中就可知晓:志远、志道、志星、志明,舜卿、震卿、善卿、仁卿。他希望子孙后代志向远大,心智通透,为人仁厚,成为国之桢干,民族栋梁。所以,在国运日衰之际,他在思考如何给古梧洞注入道德上的力量,树立精神上的信仰,铸就独特的文化属性,唯有如此才能后劲十足,培养出卓异的人才。
机缘巧合,宋端平元年即1234年的一天,唐子超听说城西古刹“慈恩寺”倒塌了,便连忙赶去察看。“慈恩”的意思正是慈母的恩情,“慈恩寺”倒塌不正昭示着母亲的恩情没有报答吗?于是,他于1234年独力迁建“慈恩寺”。
慈恩寺最初位在县西,唐咸通二年(861)建,旧名“兴乐”,治平二年(1065)改额。对唐子超与慈恩寺的关系,清光绪三年版《唐氏四房族谱》记述如下:“古刹名曰慈恩寺,原在城西二里,日就倾圮,公于宋端平解元元年徙建于本里洞內,捐金匕材,独力建修,后世感公盛德,雕塑公像于寺中,招养住持供奉香火固已自昔为昭于今为烈者也,聊志一端善举,俾后世积厚流光,方兴未艾云。” 民国《全县志》载:“慈恩寺在城东十五里,恩乡桐木冈村北,清光绪末倒塌,柱础犹存。”
由上可知,慈恩寺始建于唐代,位在全州城西,南宋倒塌,唐子超将其迁建于白宝桐木岗。光绪皇帝在位34年,唐氏四房族谱撰写于光绪三年,慈恩寺倒塌于光绪末年,前后相差二三十年。谱书修撰时慈恩寺就在身边,和尚住持俱在,香火鼎盛,完全具备真实记载慈恩寺的客观条件,没有凭空撰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今,慈恩寺的遗迹还在桐木岗,当地百姓称之为“寺边”。所以,结合《全县志》的记载,唐子超迁建慈恩寺为学界认可。广西有学者指出:“这条族谱记载,如无其他有力证据推翻,是可以认可的。唐时县西有慈恩寺,宋时倾圮,然后徙建于‘本里洞內’,今遗迹尚存,逻辑通顺。”
慈恩寺虽然最终失火倒塌,但在白宝存在了六百多年,慈恩浩荡,对安抚白宝东山人民的心灵立下了旷世之功。毕竟,古代的社会和人性始终充满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山民暴动贯穿了整个广西的历史,宗教信仰对那些不安分的灵魂具有某种制约力。慈恩寺就像一枚定海神针,屹立在全州的东部山区,树立了道德标准,塑造出淳朴、善良、平和、忍让、安宁和正直的人们。
白宝何时开文脉,唐公端举破天荒。慈恩寺的迁建,是蛮荒之地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唐子超慈悲为怀,挽古刹之倾覆,将宗教为善、至仁、至慈的精髓融于白宝岭,因而所创造的山乡文明具有世界性品格,拥有超凡卓绝的内涵,对全州的山乡文明、宗教文明以及后世子孙影响深远。
答读者疑问 还历史本原问:唐子超为南宋隐臣无疑,因为有县志提供佐证。但其广南观察使一职仅见于清唐氏族谱,有人认为族谱不可信啊。
答:唐子超究竟是不是广南观察使,究竟是多大一个官,不是那么重要,他的历史地位主要在于对全州山乡文明的本土化贡献。他是慈恩寺的迁建者,是白宝山乡文明的奠基人和肇创者,是全州恩乡的人文始祖,是全州文明史上飘扬八百年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一面旗帜。全州历史文化名人堂应有他的一席之地。对唐子超的历史定位,冠以“南宋隐臣”或“山乡巨擘”可也,既能避免无谓的争论,又能维护山乡人文始祖的尊严,两全其美。白宝人民厚道,并不争唐公为高官显贵,立天地、得民心、泽后世幸甚。
族谱是否可信,首先看里面记载的人物是否还有很多人记得。唐子超的后裔,遍及湘桂川渝,现在不下十万。此乃宝贵的财富,巨大的贡献。唐子超在白宝育有四子,长房居桐木岗,二房居莲花村,三房居乔田坊,四房居白水底,古梧洞唐氏都以唐子超为始祖。二房于元末明初迁往今天湖南老村里,距白宝二十里。经过数百年的开枝散叶,清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二房子孙奉旨垦荒,携带族谱和乡土陆续迁往川渝,分布在今天的内江、威远、安岳、乐至、资中、简阳、大足、江津、荣昌、永川、重庆等地。八百年来,唐子超一直活在族谱中,活在子孙后代的心里,每年清明节来迎马山认祖归宗的唐氏后裔项背相望,络绎不绝。而且,全州古城太平坊建有“希陞公祠”,旧谱有载,图文并茂。直到解放初期才被拆除,说明世人对唐子超的供奉和纪念早就不局限于白宝,他的名望早已融入城市发展和全州文明,并得衙门认可和百姓拥戴。请问全州祖坛,拥十万子孙者,还有谁?
古语云:十年宰相不如一日县令。说的就是立足本土、开化蒙昧、建设家园的极端重要性。全州的文脉主要是由外籍官员缔造,如宋朝柳开、王世行、师维藩、林岊,明代陈光裕、章复、吴伯璋、顾璘,他们都是宦寓全州垒筑杏坛的典范。其中,柳开乃开化全州第一人,河北大名人;顾璘是推动全州文明进入鼎盛期的一代大贤,江苏南京人。而全州籍名宦在外地做官,确实为家乡学子考取功名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他们大多数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对全州的文化文明并无直接贡献,远比不上来自外地立足全州本土的父母官。远海浩瀚却难救近火,彩虹美丽但不可披肩。名气大不等于贡献大,码清楚这点就很容易理解立足本土的价值了。南宋隐臣唐子超,扎根本土,擎起了一幅绵延八百年的山乡画卷,是全州山乡文明的一面旗帜,虽默默无闻,但功德无量。崇仰这位一心向佛的山乡巨擘,本身就是一种善良,一种文明。漠视他的功德,就是一种堕落,一种孽障。
说族谱不可信的人,往往是那些离不开谱书的人,他们史海拾贝,需要从各种族谱中找到正史给不了的答案。由于谱书,特别是新谱,质量参差不齐,对历史的记载或语焉不详,或攀龙附凤,或溢美拔高,或残缺凌乱,或错漏百出,或移花接木,读谱者内心抓狂,印象极差,于是愤恨如斯,逢人就说谱书不可信,别人家的族谱更是不可信,看都不用看。但说是说,做归做,第二天他们又埋首各种谱书,如重整县志天天看谱,时时依赖家谱,一番辛苦之后,鲜见空手而归。
自从姓氏出现以后,修谱就一直存在,或隐秘,或公开。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动荡不安,征伐不断,和平安定的岁月不足五百年:狼烟四起族谱隐秘,社会稳定家谱公开。无论朝廷是否允许,修谱护谱都一直存在,除非那个家族十分衰落,或没有礼义廉耻。以广西狼兵故里田州为例,特殊时期岑氏族人盟誓以生命保护族谱,轮流每户保管一天,夜间转移,谱在人在,谱失人亡,岑氏世谱才得以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广西土司政权的重要历史文献。每个时代都有大事发生,很多事件或一笔带过,或不被官方记载,甚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族谱对其记载更为真实准确详细生动。如清初广西全州石塘屠村事件,清政府作为刽子手不可能记载此事,得以当事方陈氏族谱和陈氏祖传为准,如今不能因为正史没有记载,就说该谱所载之事不存在不真实不能以正史地位待之。这是背弃事实原则的。
因此,对待族谱,特别是旧谱,还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不能因为世上有很多家谱修得有问题,就把天下的旧谱都否定了,这是要不得的。可以怀疑,但要认真求证,仔细甄别。特别地,当一本旧谱所记载的事件跟它所处的社会背景相关联的时候,它不只是一本简单的家谱了,而是当地的一种史料,至于是否可信当由读者、专家和当地民众评判。我们不能抱着一种狭隘的个人情绪,把这样的家谱看成一家一姓之私人领域而加以贬抑抛弃。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这也包括族谱等文化遗产。清《唐氏四房族谱》所记载的相关事项,如慈恩寺、学湾塘、观察使等,跟《全县志》等历史文献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因而具有证据效力。
人是地球上唯一奉行双重标准的物种。有位老学者说得好:“不可完全否定家乘的历史价值,史料丰实者应列为全州历史名人。”
问:有人说全州一千多年来,修志十多次,如果唐子超担任过广南观察使的话,历史对他的记载是十分详细的。
答:持此观点的人,对全州修志的历史认知不够,对广南观察使一职的认知也不够,并且忽略了唐子超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
全州修志,虽历史悠久,但清代之前的志书古已散失,今俱不传,直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知州黄志璋得前志残秩,抢救整理,为现存最早的县志,而今全秩仅见藏日本内阁文库。于是,从五代晋天福四年至康熙二十八年,全州志书断层断代有缺有失者纵跨750年。黄志诞生时,南宋隐臣唐子超已逝世445年,其志不仅没有他的名字,就连他亲手创建的古梧洞也未系统辑录,可见编撰仓促,挂一漏万,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后来者即便想东渡湘江,探访白宝源流,也因山河阻隔和出行成本而作罢。于是,路径依赖,沿袭前志,遗漏唐子超实在不足为奇。好在民国二十四年《全县志·社会》指出了唐子超的隐臣身分:“白水底唐姓宋时始祖宦全州遂卜居于此。”
千年历史,人事浩繁,岂是一部小小的县志和史书所能囊括,无数杰出的人物和无数大事件,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记载下来。古代是,今天是,将来仍是。如果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何谈传承?
以何传承?再说观察使。任此职者,看起来确实是个大官,可以巡察朝廷指定的地区,但他的真正任务只有一个,或办理大案要案,或推动某项政策,或为朝廷征集财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两头讨苦,常常受阻被弹被贬。历代观察使,往往不是由朝廷的大臣担任,更多是由具有特殊经历、特殊才干和特殊性格的一线官员临时受命。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光绪吉安府志》记载,南宋江西人曾恭甫,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司理参军,因为有器干,善于言事,用兵之际得大吏荐举,而历任河南观察副使。再看今天中央部门派遣的巡视官,受命完成一项任务,未必都有很高的级别,也未必能青史留名,这种情况多如牛毛。全国各姓旧谱对其先祖有任某省观察使一职的记载很多,而正史未见留名,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唐子超以荐举任广南观察使,毫不奇怪。他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巡察广东、广西和海南,为朝廷征集财赋、皇粮和贡品。显然,他被委任此职跟其从军阅历有关:他年轻时为司马司务,此起点比同时代的曾恭甫要高。由于唐子超直属军方或朝廷,他无需向地方衙门报备自己的行踪,故广南一带没有留下他的详细记录实属正常。而且,在他逝世三十年后,蒙古铁骑攻占临安,南宋覆灭,葬身战乱的文档不计其数,蒙军四处追杀前宋旧臣,白宝唐氏怎能寄希望于临安?
对唐子超的历史定位,凭官方的智慧,冠以“南宋隐臣”或“山乡巨擘”可也,既能避免无谓的争论,又能维护山乡人文始祖的尊严,两全其美。只要符合国家对“历史文化名人”的评选标准即可:在本辖区生活或工作过的历史人物;在某一领域有重要成就,对社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或产生深远影响;主要思想或历史著作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背景清晰,史料依据真实、可靠;主要事迹可故事化、艺术化,具有可呈现和转化的艺术空间。显然,大宋隐臣唐子超完全符合上述标准,而且比全州文化公园里明清时期的名人早数百年,对全州山乡文明的本土化贡献远超后者,其子孙后代奉旨垦荒,遍及湘桂川渝,对国家贡献巨大。
问:清《唐氏四房族谱》的修撰质量究竟如何?
清《唐氏四房族谱》明显出自饱学之士之手:文笔精炼,表述准确,情感克制,结构完整,对唐子超的身份、生卒、子嗣、兄弟、居所记载清晰,并无拔高夸大之辞。该谱记载唐子超“宋理宗时选登仕藉授中宪大夫以荐举任广南观察使”,信息量很大,既指明了所任职务,又指出了任职途径和背景。如果要想拔高唐子超的功名,只需把“中宪”改为“正议”“通议”“嘉议”,或“资德”“资政”“资善”,其官阶即从正五品跃为正四品或正三品,而且看上去更匹配广南观察使的职务。如此改之,轻而易举,但作者并没有这样做,此诚如实记载也。另外,唐子超出身司马司务,军人未必在科举道路上取得过很大功名,进士册上查不到他的名字很正常,跟他“选登仕藉授中宪大夫以荐举任广南观察使”征收财赋,不仅毫无矛盾,而且更加顺理成章。综上,清《唐氏四房族谱》的内容是严谨的,可信的,经得起历史检验。
清《唐氏四房族谱》对唐子超之弟记载如下:“希晚公,第二十四郎,妣卿氏,合葬白水底田中心。希华公,迁居恭城县地名唐王桥,妣李氏”对唐子超的配偶也有记载:“妣粟氏,系宝府全美公之女。”宝府何在?粟氏祖婆究竟来自哪里?谱书上没有说明。对此,粟氏文化研究会的专家指出:你们老祖粟老太婆,十有八九就是全州粟家营的宗亲。粟家营在学湾塘上游数百米,现在只剩下粟家渡却无粟姓;粟家渡地处湘桂古道的水路交汇点,解放后粟家渡建了东门大桥。由此我们可以推想,粟家渡是一个重要的财货集散地,唐子超的妻子“粟氏”出自粟家营,这是他没有东归留在全州的原因之一。唐子超在七十岁的时候,能独立迁建慈恩寺,说明他是极富的人。他的财富来自哪里?肯定不是来自白宝岭那几亩贫瘠的土地,而是来自他特殊的工作和特殊的津贴。南宋政府实行高薪养廉,官员俸禄优厚,想必希陞公有一笔巨大的积蓄
。还有,根据《唐氏四房族谱》记载,今全州“岳湾塘”或“岳王塘”实为“斈湾塘”的误写,应予以纠正。斈(xué),同“学”,学校学习、吸取经验之意。岳,本指高大的山,后特指五岳,显然是误写,用在那里不合适。每个古老的地名都有其深远的来源,凝聚着先民的典故和智慧,叫错地名无异于错失历史。而今,学湾塘已成为湘源文化公园的所在地,舜帝像屹立于岸,名人群雕坐落于此,百年全高依偎在旁。因此,将“岳湾塘”正名为“学湾塘”势在必行,既能以雅释古,又能融古通今,名实相副。
清代《唐氏四房族谱》对慈恩寺和学湾塘的记载,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填补了全州历史文化的些许空白,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虽然因循守旧是人的天性,但只要打开心锁,就能拨云见日: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问:你对官方作何期待?
答: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州文化公园的建设,正在熔化这种开阔的哲学思想,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空前壮后,必须给以无尽的赞美。在后续的建设中,她的一个重要价值,应该是要容纳那些稀缺而又真实的存在,容纳奇崛的山乡文明。
白宝唐子超,《全县志》载其为南宋隐臣,他是白宝山乡文明的奠基人,是慈恩寺的迁建者,是古恩乡的人文始祖,是全州文明史上飘扬八百年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一面旗帜。白宝唐俨,为唐子超第九代孙,他割臂救父,是中华孝道文明的典范,是神一般的人物,无数名儒巨公颂扬他,赞美他。全州古六乡,恩乡占半边:没有唐子超,全州南宋的山乡文明将失去半壁江山;没有唐俨,全州的儒家孝道将要在平平无奇中徘徊数百年。这不是虚夸,是如实描述。
文化文史文宣,当有大将风度,当与天下后世争雄,一正一奇王者之道也。唐子超和唐俨,乃全州文明历史上的优昙奇花,祥瑞奇异,近世罕见,全州历史文化名人堂里应有他俩的一席之地。
作者:唐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