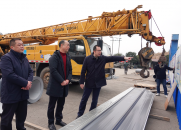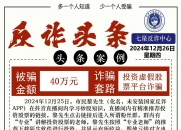据统计,2018年我国已经有超过7700万独居状态的“空巢青年”,而在今年,这一数据将会上升到9200万。 人民智库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空巢青年”是主动选择独居。其中,“想有自己的隐私空间”因而选择独居的占比47.5%,“自己的生活作息和别人不同,不想受到他人影响”所以选择独居的占比39.2%。选择“一个人生活很方便”和“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单纯地想体验独自生活”的“空巢青年”分别占比33.5%和32.2%。

那,什么是“空巢青年”? 其实顾名思义,“空巢青年”一词由“空巢老人”演变而来,指的便是远离父母亲人、独自一人居住,年龄介于20岁至39岁之间,在大城市单身打拼的年轻人。 一言以蔽之,“空巢青年”的生活那就是——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四季淘宝,五谷不分。快看看自己,你中枪了吗?

当然,也有一些更精准也更扎心的“空巢青年”画像:大学毕业,在一线城市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体面工作,住 18 平米月租三四千的一室户或群租单间,唯一熟悉的室友是自己养的猫或狗。 饮食主要靠便利店和外卖,衣服里最看重品质的是睡衣和内衣,周末习惯肥宅一瘫两天就过去了。 他们中有的人文艺且丧:“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有的人则是沙雕快活:“喝个下午茶,啃个大西瓜,空巢青年乐开花”。

关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褒贬两种声音自然也是不绝于耳。有的网友无奈地吐槽起买房、996和婚恋的三座大山,把“空巢青年”看作是一种社会内卷压力下年轻人无可回避的苟安之举。 有的网友则反思到,“空巢”是每个人人生阶段的必经时期,人总是需要这样一个阶段完成从“半自治”到“自治”的转变,与原生家庭分离并且真正承担起自我管理的责任。 问题来了,你是“空巢青年”大军中的一员吗?你又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先别忙着给出答案。如果眼下的现实会让你感受到焦虑难安,我们不妨先暂缓一阵,将目光投向200年前的一位狠人。 这位明明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却一直对工作厌恶至极,始终渴望着绝对自主的生活,为此似乎放弃一切都在所不惜——他不结婚不信教不选举;他不打工不纳税不致富;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 从教师到土地测量员,他始终坚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写作,而他的文字,却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心灵栖居的故乡。 说到这里,想必各位读者已经猜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梭罗,瓦尔登湖畔的隐者。
01
从何时起,开始向往独居? 对故乡康科德的眷恋,让梭罗似乎早早地就拥有了一种“待在家的真正天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个肥宅它不香吗? 也正是得益于早年间在故乡形成的对自然的深情厚谊,成年后的梭罗依旧保持着对自然风情的热爱、以及对离群索居的偏好。他然,克制,对社会冷漠以待,他在文明人中找不到共情之处,就到荒野的大自然中去寻求: “我感觉,我的生活非常简陋,我的快乐非常便宜。快乐和悲伤、成功和失败、辉煌和卑微,的确,很多英语词汇在我这里的意义与在我邻居那里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我发现邻居带着同情心看我,他们认为是卑微和不幸的命运让我总是到旷野和森林中去,让我在河上独自划行。但是,我在这里找到了极乐世界,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独居生活的第一步:心理建设,完成!毕竟那个时代不同于当下,选择离群索居需要勇气,更需要面对社会普适性的评价压力与旁人的指指点点,所以,想要真正让心灵拥有一片独居的空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拥有一套独属于自己的评价标准,让自己在这套标准体系中自得其所,而不是陷于社会的成功学旋涡之中。 也是在这一时期,钟爱自然的梭罗也会叫上朋友们四处游山玩水。在沃楚西特山散步,他感慨这座“在群山之外,兀自独立”的高山,像极了孤独的自己;在斯塔滕岛上看潮起潮落,他则幻想“我的人生就像是海滩上的一场漫游,向着大海的边缘不停行走”;而在几次造访朋友之后,梭罗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愿意牺牲哪怕一丁点儿个性去屈从于社会:“我想,我宁愿在地狱里有个单间,也不愿在天堂中与人共眠”。

于是,1845年,28岁的梭罗选择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坐标:瓦尔登湖畔的小屋—— “我去林地是想要过有目的的生活,只去面对生命中最本质的事项,并且要搞明白我是否能学会它教导我的一切,而不是相反,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未曾活过。我不想过一种不是生活的生活,生活太昂贵了;我也不想听天由命地生活,除非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想要潜泳到生活的底部,汲取生命全部的意义,坚定地生活……将生命逼到角落。”
02
选择独居,做大自然的单身汉
瓦尔登湖北岸树林边的斜坡,静谧、幽远,一英里之内没有人家,既可以静思冥想,也不耽误随性而行拜访亲友,这里便成了梭罗的圣地。 在这惬意的环境中,梭罗常常选择早起到池塘中沐浴,之后便开始一天的工作或是休闲。想要工作的时候,他在小屋周围开垦播种,日复一日在豆田里劳作。(陶渊明:为什么隐士都爱种豆?)而当他不想劳作的日子,便可以嚣张地表示不能“为工作而牺牲当下的美好,无论是动脑还是动手”: “有时,在夏日的清晨,照常洗完澡之后,我便坐在阳光明媚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时分,此时此刻,万籁俱寂,只有我独坐在这松树、山核稠阙和漆树林中,凝思冥想,偶尔有鸟儿在附近啁啾,或悄无声息地掠过我的屋前,直至太阳落山,照映在我的西窗上,或是远处公路上传来阵阵游人的马车声,我这才想起时光已匆匆流逝了。我终于明白东方人所言的沉思和无为了。总的来说,时光如何消逝,我不在乎。”

当然独居瓦尔登湖畔的生活里,除了富足的惬意的心灵,以及日臻完善的清雅文风,梭罗也并不是没有访客。当他沿着湖畔森林的菲茨堡铁路行进时,火车司机们经过时都会像问候一位老友般像他鞠躬。 爱默生、钱宁、阿尔科特、霍斯默,这些文学家与哲学界常常能伴着梭罗在小屋中安然沉思,而对于那些沽名钓誉的慈善家,梭罗便爱答不理地直接出门干活儿。 而更有轶事传闻,认为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地下铁路里帮助了不少潜逃去北方的黑奴。看来,这位抱怨着“社交太过廉价”的隐者,却也有着不厌世的温情与通透。

总之,在这里安静的沉思结出了硕果,成熟的梭罗也完成了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瓦尔登湖》,而对于这位沉思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对于自己超验哲学的检验: “如果一个人自信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进,并努力过着他所想像到的那种生活,那么他就会遇见在普通时刻里意料不到的成功。当他简化自己生活的时候,宇宙的规律也会对他相应地变得简单,孤独就不再是孤独,贫穷也不再显得贫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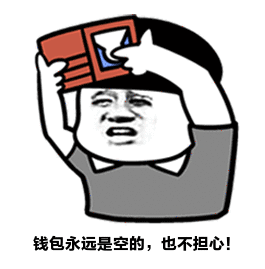
03
看穿生命的外壳:独居,在哪儿都可以 1847年9月,梭罗离开了陪伴他三年光阴的瓦尔登湖,回到了父母的居所。对他来说,离开森林和去到森林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重要的是,他体验到了种种他想要的生活方式。 而后他也常常出去短途旅行,渴望“在雨中以云杉为屋”,在独立、简单、冒险的旅程中享受山林。最终,这位充满才气又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在44岁英年早逝,然而,他留下的思想火花却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 梭罗独立、自主,反对一切哲学教条或是伦理体系;另一方面,他又乐观、坚定,在书中时时刻刻不忘提醒人们,要对自我的人格具有满足感,不要浪费时间去思索过往,而要活在当下、相信未来。

平静、乐观、纯洁,因此,便也不难理解梭罗对于忙碌的反感。在梭罗的体系中,现代社会追逐私利的热切与躁动、忽视或无视思想沉静的需要的现状,便是所谓的“忙碌”。(是不是让你联想到了内卷、996、打工人?)在梭罗看来,“忙碌”便是诗意人生的对立物,是对生命本身的否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梭罗否认了努力工作对于心灵和道德的重要性,而是说,梭罗更提倡一种闲暇与自由的发展空间,让每个人独立自由发展的品性不被生存斗争压垮和扭曲。 总之,这位看穿生命的外壳与表象的理想主义者,看到了对多数人而言只是梦想和幻想的真实,以心灵的独立纠正大众的虚妄,却又始终笃信人类的理想与进步。对他而言,瓦尔登湖凝聚了时间和空间,一瞬即是永恒。正如他在《马萨诸塞州自然史》中所写到的:
“在循环往复的艰辛生活中, 也会时常绽放出蔚蓝的天空。 紫罗兰一尘不染, 银莲花被春风吹散, 飘落在蜿蜒流淌的小河旁边, 这一切使得那旨在抚慰人们的悲伤的最好的哲学 也顿时变得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