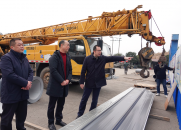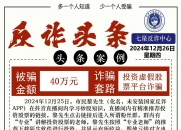电影《卡迪亚的姐姐》
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5日下午7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上,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尔瓦和作家btr以“童年、真相和创伤——深入黑暗”为题展开对谈,诗人、学者戴潍娜担任本次活动的主持。
在对谈中,巴尔瓦与btr聊到巴尔瓦的作品《光明共和国》与《小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进一步了解。
以下为本场对谈的实录,理想国经授权发布。
回看对谈视频
戴潍娜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线上沙龙活动,我们今天这场沙龙请来了两位非常风格化的作家,他们似乎都在主动地去回避一种专业作家的状态,去回避一种行家里手的职业状态,努力跳脱出文学的惯性。
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西班牙的作家,安德烈斯·巴尔瓦(Andrés Barba)。他的小说《卡迪亚的姐姐》(Het zusje van Katia)被改编为了电影,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略萨也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说他“早已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早已拥有了一门与其年纪毫不相称的精湛技艺”,他的作品《光明共和国》和《小手》也被理想国翻译到了中国,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两部作品。

安德烈斯·巴尔瓦 西班牙作家。他的小说作品包括《小手》,《特蕾莎修女》(获巴列斯特尔奖)和《一匹马的死亡》(获胡安·马奇奖)。2017年,他因《光明共和国》赢得了赫拉尔德奖。巴尔瓦被格兰塔杂志选为“最杰出西语青年小说家”之一。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中方作家,来自上海的作家btr先生,我也是几分钟前刚刚得知,他的名字btr来自一部马其顿电影,《暴雨将至》(Before the Rain)。他拥有非常奢侈的跨界身份:大家对他比较熟悉的是他是保罗·奥斯特的中文的译者,同时他也是《天南》杂志的翻译,他还有更加多重的身份,他是艺术评论人、艺术策展人,也是小说家,并且我们能在很多的媒体上看到他的专栏文章,是一位非常跨界、多元的作者。

btr 作家、译者、艺术评论人,著有《迷你》《意思意思》等。(微博@btr_)
这两位都非常酷的作者身上有一点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富有游戏精神,很会在文字里面玩一些崭新的感觉,好像两位都在尝试去打破虚构的边界,到最后却给我们一种比真实更高的真实,这种对虚构的打破并不是情节上的,而是感知上的,就像是在不断地打开一个已经沉睡已久的感知世界。那我也想听听你们二位对彼此作品的感受。
01
btr :我最近把巴尔瓦先生的两本书都读了,然后我非常喜欢,前面戴潍娜讲的这两个关键词,在我看来非常地精准:
其中一个是游戏,我相信游戏这件事情贯穿在了巴尔瓦先生的整个创作,无论是《小手》当中孤儿院里的游戏,还是《光明共和国》里作为一个共同体发明出来的游戏。这些游戏开始于何处?这些游戏的边界又在哪里?这在巴尔瓦的作品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可以说,当这些游戏渐渐超越了游戏的边界,变成某种意义上的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突然地惊悚起来,我读这两本小说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是讲到感知,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经常在马路上乱逛的人,在丰富多彩的城市里,如果去感受的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维度的东西,比如说城市的气味、城市的声音、晨曦的色彩等等。那么这些感知在巴尔瓦先生的作品里面,常常是通过写孩子来表现,我觉得孩子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在没有被完全驯化之前有一种灵气,他们的感觉是都是非常敏锐的。所以我觉得感知和游戏都是我们理解巴瓦尔先生作品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巴尔瓦 :我没有办法读到btr的小说,所以关于btr先生,我唯一能够说的一点就是,他对许多不同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兴趣,比如烹饪、艺术、小说、新闻,应该说,他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我指的是,总是对不同的领域持开放态度,总是保持敏锐,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对一切与人相关的事情都感兴趣的作家。
戴潍娜 :我觉得这两位作家都是作家当中的魔术师类型的作家,那我有两个问题分别问二位。
首先是巴尔瓦先生,因为我读过您的《小手》,我觉得它原本是一个极端残酷的故事,但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却会不自觉地获得一些甜蜜,甚至是美妙的幻觉,您自己也曾经说,这是一个反乌托邦的小说,但是最终它被写成了一部乌托邦式的书,建造了另外一个失之乐园,我想请您具体来谈一谈这种乌托邦式的写作。
巴尔瓦 :《小手》和《光明共和国》就像是两本完全不同的小说。
《小手》是真实的故事,这件事发生在孤儿院里,一群五六岁的女孩真的杀死了另一个女孩,把她的尸体做成了一个洋娃娃,在院子里玩了四天。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时,我真的被它吓坏了,但同时,好像有什么东西让我产生了怀疑,怀疑这个故事里真的有爱。我总是对这样的情景和主题很感兴趣,它们第一眼看上去很糟糕,但当你靠近时,它们又变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光明共和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群孩子来到南美洲的一个殖民小镇。一开始,他们对社区来说是一种威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体面而平和的社区,而这些孩子野蛮又暴力。但是,这本书里作为叙事者的公务员显然低估了这些孩子。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们展示了乌托邦和快乐的孩子们的社区原来可以是这样的。
我一直对这类东西很感兴趣,生活中的主题、经历和故事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并让我们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有多么混乱。对于很多事情来说,在童年期间都只是一个空白的范畴,我们对童年的概念在历史上是如何变化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思想史上,至少在西方文明中,从罗马帝国到现在,我们对童年的一般性看法,比如童话故事,比如小孩子需要被保护,以及许多其他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观点,其实并不是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东西,例如,“童年是快乐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童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虚构,一种我们编造出的叙事,来让我们相信人间有天堂,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经历过了。
戴潍娜 :巴尔瓦先生刚才谈到了一些非常深刻、非常内核的文学本质,就是不同的视域将创造出不一样的世界,而文学恰恰是超越此刻的政治建构和文化建构的,因此一种游戏式的文学态度往往可以对此刻构成某种冒犯,或者说是超越,而这个我们此刻正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许只是小说家的一场虚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艺术化的观点,那同样的,btr先生也做了很多的展览,所以我也想请btr谈谈从艺术而来的文学养分。
btr :我在想,可能跟中国大陆这些年以来的艺术发展有关,造了很多美术馆,整个艺术圈都非常活跃,所以我接触到了很多不管是中国本地的还是西方当代的一些艺术作品,这些东西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刺激了我。比如说一只奶牛,它产的是奶,但它吃的是草,并不是吃奶产奶。所以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我不用看很多小说然后才能来写小说,我可以看些别的来写小说。比如说这是一个图像的时代,那么艺术啊,电影啊,乃至你在网络上随便看到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的养分,对你会有一种写作上的刺激。
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艺术已经用某种方法对现实做过处理了,那么它跟文字之间其实是有不同的,归根结底是一种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写作有它本身的限制,因为我们使用的材料是文字,但是艺术,它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它可以使用图像啊,声音啊,它也可以使用文字,而且它可以把这些做成一个组合,所以这么一来,我就渐渐开始把一些艺术评论写成小说,后来又把一些小说写成艺术评论,然后又跟设计师合作了一些界限不太明显的书。
我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迷你》,拿在手里非常非常小,然后它的六个面上都印了各种各样的图像,里面其实是我写的一些非常小的短文,只有一两百个字,旁边是设计师根据短文翻译成的图像。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玩法,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人在写小说,很孤独地玩,现在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把一种私人创作转化为一种集体创作,一种跨界的艺术形式,就比较开心。
戴潍娜 :两位作家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各自新颖独特的玩法,我觉得里面都有非常奇妙的艺术观点,我想二位是不是也对彼此做一个回应?
巴尔瓦 :btr展示的书很美妙,因为我自己也和艺术家一起写了很多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和艺术家一起工作是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因为对同一件事情,你可以得到另外一个角度的观点。
这幅画实际上是我和一个艺术家朋友合写的一本书的一部分,它的主题是“坠落”,我很喜欢这个概念,人们从高空、从太空坠落,关于你死前最后一刻的意识,你知道你会坠落。我们把他的照片放在一起,他制作了人们在太空中坠落的一百多幅图片,那是一次美好的经历。
我完全同意btr先生关于玩游戏的观点,以及游戏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地严肃和重要,作为作家或艺术家,以一种游戏的态度,一种玩笑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生活中做严肃事情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当成游戏来玩,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btr :刚刚巴尔瓦先生讲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其实,作为一个作家,写作跟艺术的关系,其实跟它和生活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我自己是保罗·奥斯特的译者,保罗·奥斯特跟一个法国女艺术家苏菲·卡勒有一个合作,苏菲·卡勒邀请保罗·奥斯特给她写一个故事,她说我在今后一年里就按照你故事里的样子去生活。保罗·奥斯特觉得这个工作的责任太重大了,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所以他就不敢这么做,只是给苏菲·卡勒写了几条建议,就有点像行为艺术,比如说见到人怎么问好啊,还有把一个电话亭改装成一个什么东西啊。苏菲·卡勒后来就把这个做成了艺术。
后来又有一个西班牙的小说家,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他也写了个小说,虽然苏菲·卡勒并没有请他去这么做,但是他为她写了这样一部小说,等于是想象了她的生活。生活、写作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在这些例子当中就变得错综复杂了。我也从比拉-马塔斯身上得到了很多灵感,因为他后来也去写了他去卡塞尔文献展的经历,叫《卡塞尔不欢迎逻辑》,这书也是虚实难辨,看起来像是一个展会的游记,但其实很多东西是虚构的,但里面的有些作品又是真实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写作、生活本身的边界就变得非常模糊,也变得意味深长。
另外,我刚刚想还想讲一个就是,对于游戏来说,我最初的游戏感有一个来源,就法国的文学团体“乌力波”(Oulipo为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缩写,音译“乌力波”,直译“潜在文学工场”,是一个由作家和数学家等组成的打破文本界限的松散的国际写作团体),他们就是通过对文本施加限制来焕发更多的创造性,这些创始人很多是数学家,所以这个游戏最初是基于一些数学逻辑来写作的,也是一种集体写作的游戏,今年正好是乌力波六十周年,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主要的灵感来源。
02
文学就像病毒,总能找到机会活下去
戴潍娜 :两位都抛出了极其有趣的文学观点,文学、艺术、生活,三者不是简单的彼此模仿的关系,而是像一个多棱镜,在彼此折射、彼此影响、彼此渗透。刚刚btr先生提到的乌力波也是我个人特别关注的一个文学团体,当年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作“潜在文学工厂”,创始人雷蒙·格诺曾经写过一首无止境的十四行诗,叫《一百万亿首诗》,它是由十首十四行诗组成的,但是十首十四行诗里面的每一行都可以进行自由的组合,如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在阅读这首诗,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都没有办法读完,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文学实验。
谈到这里,我想继续来追问两位:你们心目中潜在的文学将会是什么样的?它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实验形式去跟其他的艺术形式进行结合?我们今天都在说文学衰落了,那究竟是文学在不断缩小自己的边界,还是说潜在的文学已经渗透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形式中,跟更多的艺术形式进行了结合,它的边界在不断扩大呢?
巴尔瓦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多年了,就像文学的死亡即将来临之类的观点。没关系,我的意思是,小说并不重要,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继续写小说、读小说,我认为文学很快就会消亡只是我们的一种幻想,这种观点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事实上,文学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这些类型之间的界限都在改变、模糊,但的确,我们越来越难让自己专注于阅读一本书,因为有太多东西在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电影、邮箱、朋友的电话,就好像周围有很多东西。大约十年前,在翻译《白鲸》的时候,我心想:好吧,现在还有谁会读这本书呢?我的意思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从头到尾地读完《白鲸》吗,还是说我们再也不可能读完《白鲸》了?如果我们不再有可能从头到尾读完《白鲸》,那我们身上究竟会发生什么?作为一个读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失去什么?如果说我想从中获取某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形式上变得越来越小是有道理的,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它迫使我们集中注意力,更准确地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
巴尔瓦翻译的西语版《白鲸》
我认为文学总是在寻找不同的途径以存活下来,就像病毒一样。文学就像是某种我们都有的病毒,我指的是人类的本性,人类本质的心灵结构需要文学,我们需要它来解释世界,解释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解释我们的感觉,所以我认为文学会告诉你,它会找到生存的方法的。我们将永远拥有文学,只是或许是以不同的形式——它可以改变形式,当然。我们的心灵活动中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文学,所以我们有理由保持对生命的希望,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那样,要玩得开心,我指的是跨越文学界限的那种玩乐,探索文学本质的极限,认为事物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而不是封闭的,死气沉沉的。
btr :刚刚巴尔瓦先生讲到病毒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比喻非常精彩,然后我觉得文学也许需要一些病毒营销,这样才能卖得好一点。
然后我是想到这样一点,时代的确是变了,其实十年前还没有多少人用iPhone,社交媒体还不像现在那么发达,而现在,社交媒体的高度发达,人人都拥有智能手机,这件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至少在中国,我们已经很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情都是发发微信,发语音或者打语音电话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礼貌的,现在大家默认的礼仪规范是打字,所以其实我们比以前更多地使用语言,但是不是就意味着文学就变得更发达了?好像也不是。我们经常说文学死了,但文学已经死了太多次了,我们都知道它死了,反正还会复活的,不用太担心。文学就像猫一样,它会不断地重生,它有好多条命,不会一下子死掉的,只是它要活下来的话,要做些自我更新。
其实文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比如在巴瓦尔先生的作品中,我都能够体会到这点,因为他写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不断插入一些声音,在引号里面,就像电影里面的平行蒙太奇,这样来处理两个不同的事情,在同一个段落里发生。有一些画面,我记得非常清晰,在《光明共和国》里有一个场景,“我们像两只萤火虫似的待在那个房间的暗处”,其实是一个非常影像化的画面,这种养分不知道是不是从电影里来的,但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文学已经部分地带上了电影的特质,不同媒介之间的互相学习可以使文学变得更新,更契合这个时代。包括《光明共和国》的最后,那个大厅里的镜子,那种碎片集合成的光,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时代的隐喻,我们现在要文学,已经不能像古典时代那样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了,而是要这些不同碎片的组合,才能成为一个光明的共和国。
03
戴潍娜 :二位都提到了文学的自我更新以及对这个新世界的适应,那我也想问一问二位,疫情对你们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你们认为疫情之后的这个世界,究竟是打开了更多的感官,还是封闭了更多的感官?
巴尔瓦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住在纽约,不得不搬到马德里,那是当时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然后又从马德里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说在疫情期间,我们绕着全世界飞了个遍。
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刚完成了一本书,我问自己,如果我没有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完成这本书会发生什么呢?因为我感觉我的想法改变了很多,我对这个故事的思考有了很大的飞跃。我已经感觉到,在疫情过后,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同的感受。那时候我正在翻译丽贝卡·韦斯特的一本小说,写于二战之前,她在这本书里讲到了所有的词,比如说,生活,爱,死亡,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仿佛是自然而然的词是如何一天天变得“过时”的。战争发生时,有一些创伤性事件使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失效了,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种状况中,现在我们可以依然可以用前疫情的方式来思考战争,但在用来写作的词汇中,有一些词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了,这些词语指向的已经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需要新的词语来描述我们现在新的心境,所以我认为这是真的,一些深刻的东西被改变了。
我们很难知道这种变化有多深,以及它们将如何改变文学。假设我们在疫情之前写成的所有小说都将会在一年半、两年半以内出版,但五六年后呢,会发生什么?那时的文学将会是什么样的类型?这种全球经验将会有怎样的影响?不仅仅是关于死亡,还关于这个世界的崩溃,系统性的崩溃,所有我们面临的最新的原则都要求一种新的语言,我完全同意,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btr :一开始,有人叫它武汉病毒,但这显然是带有歧视性的,以及政治不正确的;后来,英文世界统一成了COVID-19,听起来像是2019年的事情,就好像它作为一种病毒,如果也有保质期的话,可能保持三年就要完蛋了,可能2022年这个病毒就完蛋了;对中文来说,中国人又用了一个词叫“新冠”,这个缩写避免了任何负面的东西,因为“冠”让人想到的并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冠军”,“新冠”在中文里听起来有点像“新的冠军”。所以我觉得命名这件事情潜在地反映了一些心理状态,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
有一些事件就是很容易把生活划分成“之前”和“之后”,新冠就是其中之一,我今年做了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把上海几乎所有的公园逛了一遍,大概有六七十个,然后做了一个三分屏的录像装置,最近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展出,这个装置就叫Alone Together,就是“在一起孤独”的意思,很多动物,很多孤独的人,他们在疫情期间的状态。911之后有很多“后911”小说,以后肯定也会有很多“后COVID-19”的东西,到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可能会更有意思。
戴潍娜 :我们今天也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去展开了这样一场对话,在对话当中创造了一种真实,创造了一种叙述,创造了一种现实,也创造了一种疗愈。也期待在未来也许是三五年后,我们可以再次回顾这场疫情对我们写作的影响,回顾今天这一场未完成的对话,同时也是无尽的对话,再次感谢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