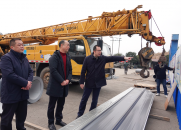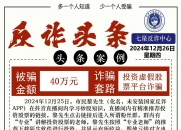|
“漆” 字,是一个象形字。
你看它上为漆“木”,中间割“八”字形,下端流出漆液,形容的是采集天然生漆时的情景。
时至今日,采集天然大漆,还得沿用7000年前的手法:画八字形采集,务必小心,以免伤及漆树根本。
每次采漆时,3000颗漆树才能集齐1公斤生漆。
因此,业内也有“百里千刀一斤漆”的说法。
现在说起漆,大多数人会联想到有刺激性气味的化工产品,雅一些的朋友会想起日本漆器。
甚至在英文里,japan也被用来指漆器。
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国才是漆器的故乡。
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我们就已经会制作并使用漆器了。
到了唐朝,我们开始与日本在漆器的技法上有些交流,也流传了许多不世珍宝到日本。
于是,日本将漆艺进一步推向极致奢华,并传承至今。
而可惜的是,作为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近年来我们却将它几近遗忘。这颗明珠被掩埋在历史的滚滚尘埃里,如同那把著名的“破琴”。 ▲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现藏于日本 宫内厅正仓院北院)
上世纪初,故宫收归国有后,工作人员在养心殿南库墙角发现了一张被遗忘很久的古琴。
当时,琴上既没有弦,也没有琴轸,琴面还积了一层厚厚的污垢,看上去就像漆面脱落殆尽的样子,破败不堪。
于是,工作人员将它登记为“破琴一张”,仍弃置于原地,继续沉沦了二十多年。
直到1947年,这张所谓的“破琴”终于被收藏家王世襄先生发现。经鉴定,这把疏于保养的“破琴”乃唐琴极品——大圣遗音琴。
幸运的是,大圣遗音琴表面包裹了一层大漆,不仅完整地保护了琴身,还在褪去陈年污垢后丝毫无损、依然光亮可鉴。
这把被埋没的古琴,终在1200多年后的人间再绽光彩,成为故宫最珍贵的古琴之一。
由此可见,大漆赞歌所言非虚:
“生漆净如油,宝光照人头; 摇起虎斑色,提起钓鱼钩; 入木三分厚,光泽永长留”
最后一句说的就是天然大漆坚韧不败,历经千年风霜而不朽的特性。
到了200多年前的明清时期,漆艺文化并未没落,行业更是名家辈出。
清乾隆年间,有个叫沈绍安的漆匠,到县衙修复一块金字匾额时注意到,这块匾的金字已褪色,但由大漆裱褙的底坯却坚固如新。
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既然大漆裱褙如此坚固,那么,大漆能不能脱离胎体,独立成器?于是,天资卓越的漆匠沈绍安反复多次试验,终于造出了最早的脱胎漆器。
脱胎漆器,是与北京景泰蓝、景德镇瓷器齐名的中国传统工艺“三宝”。
清光绪年间,精美的沈绍安漆器进贡宫廷,随之在奇珍异宝中脱颖而出,深得慈禧喜爱。
此后,沈氏漆器频繁代表中国工艺参加各类国际展会,屡获大奖,使福州脱胎漆器声名远播。
朱启钤在《漆书》中记载:“外国人嗜沈绍安手制品,视同古玩,值虽千金,亦无吝啬。”
然而社会变迁,以沈绍安漆器为首的福州漆艺行业历经数度起伏。
尤其是近20年,漆厂相继倒闭、行业标准缺位,导致传统的大漆制品日渐式微,实在令人扼腕!
明明是漆器的故乡,大漆却沦落到鲜为人知的地步。
面对福州漆艺行业的黯淡景象,出生于福建的爱国华侨林正佳先生,怀揣着复兴福州漆艺的梦想,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讲好家乡的“漆艺故事”。 2012 年,林正佳收购了福建沈绍安脱胎漆器有限公司,又与各大美术院校、漆艺行业协会等权威机构开展合作,共同探索大漆技艺和漆艺文化。
如今的沈绍安漆艺,依然恪守百年前的祖训,精工细作,还吸收了更多现代工艺的优点,使漆器更为精彩、美妙。
以这一款以银为胎、大漆髹(xiū)饰、金箔镶嵌的大漆银杯为例,每件成品都要经过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中间一些细节调整更是不计其数。
这款大漆银杯有黑、朱双色。
由中国非遗脱胎漆器代表性传承人、福建省沈绍安漆艺研究院首席漆艺大师——郑修钤先生亲自设计并指导制作。
郑修钤先生尤其擅长漆画、漆艺。 他的漆器作品《鹤鸣》曾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漆画作品《春、夏、秋、冬》至今依然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还有许多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数个艺术博物馆收藏,并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美术》等30多种刊物。
天然大漆,大美绚烂。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这款郑修钤先生亲自设计的大漆银杯,需要经验老道的匠人历经几十道工序全程手作,工期长达70余天。
不仅如此,制漆对环境的要求极高——湿度太高会颓,湿度太低会裂;而即便是同样条件下同时制作,形成的颜色也可能各具秉性。
大漆银杯采用的是沈绍安漆器擅长的“变涂”髹饰技艺。一半人作,一半天画,人与天然共同挥洒杯子的纹路。
因此,每只杯子成纹都独一无二,变幻万千,恣肆天然。
但凡接触过漆器的人,都能感觉到漆器表面那层内敛而深层的内蕴之光。这缘于漆器的最后一道程序——推光。
推光,即推磨出光泽感。待漆完全干透后,用手掌蘸植物油拌细瓦灰(或钛白粉)反复磨擦漆面开始推光;再上漆,再推光,如此反复多次,漆器逐渐出现自然温润的光感。
掌心的温度与力道永久定格在漆器之间,散发着真正手工艺品才有的气质——这是匠人把70余天的时光与心血,凝成了这只杯子的模样。
大漆银杯,顾名思义,杯子内部以净重20g的99.9%纯银为胎,大漆覆盖其外,融为一体。
这与普通漆器以木为胎,再用漆髹饰,或胶水粘黏的工艺有本质区别。
杯子的银胎压印莲花、兰花点缀,高洁幽雅。(荷花杯现货仅余30只,兰花杯暂时售罄,新一批将于2月初制作完成)
这只茶杯外部金箔变幻万千,大漆内蕴深沉;内部银胎温润儒雅,花纹精巧灵动。
整只杯子大气流畅的设计、珠圆玉润的弧度,使其天然带着一种流动的美感,恣意随性,潇洒自如,颇具文雅风趣。
沈绍安脱胎漆器,色彩瑰丽、光亮如镜,历百年依然如新。
郭沫若也曾为之倾倒:“天下谅无双,人间疑独绝”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漆银杯的色泽不仅不会黯淡,反而愈见其华。埋在内里的底蕴层层焕发而出,呈现出丰富而纯粹的莹润质感,叫人把玩痴迷不已。
岁月会让珍贵的质地更有分量。
当大漆的温润含蓄邂逅茶道的和美仪式,两种悠久的文化在现代相逢,这只大漆银杯,是颇具底蕴的饮茶雅杯。
中国人讲究饮茶之道,而茶具本身的艺术感也是茶道的重要组成。
茶圣陆羽曾写:“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
银器洁净,用来泡茶,不会破坏茶叶本味,还能令水质若丝绢,且茶久放而不馊。
用大漆银杯饮茶,自然可以保持一种优雅清净、细品香茗的氛围,更能展示主人卓越的审美情趣。
漆器,是天然生漆脱胎换骨的蜕变。
采漆的艰苦困难,工艺的精巧繁复,注定了它一开始只能是贵族用品,很难走进寻常百姓家。
然而,它轻巧而坚固,即使饱经风霜仍历久弥新,又特别适合日常使用,更可以传家、传世。
沈绍安首创的 “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于 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沈绍安品牌的多款漆器在众多拍卖中,也拍出了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的价格。
沈氏漆器,凭借过硬的品质、精致的技艺、超高的观赏收藏价值,至今可谓是荣誉等身——
福建金牌老字号 福州市知名商标 2019“最具品牌影响的老字号企业”称号 2017 首届中国世界遗产金狮奖工艺美术类金奖 2016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2015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第八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华工艺精品奖最佳技艺奖、金奖…………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