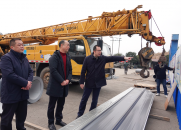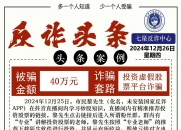全州的地理,一言蔽之,主要是湘江、灌江、万乡河与越城岭、都庞岭、海洋山这“三江三山”。三江三山相近相连,难免存在一点误读。比如横跨凤凰、安和两镇的天子岭,蕉江的宝盖山,本属于海洋山山系,却被认作是都庞岭的山脉。其实纵览地图,以湘江、灌江析分三山,很明了。海洋山处越城、都庞二岭间,呈西南-东北走向,自恭城、阳朔北上,经灵川、兴安延伸至灌阳、全州,最高峰即宝盖山。越城、都庞在华南“五岭”之列,名头自古响亮,海洋山跨度虽不少而名声不大,误读或源于此。
徒步天子岭(网络资料图)
天子岭仲春-经中心摄
位于海洋山北端的天子岭,一溜长长山脊或隆或峭,奇峦妙石,气度非凡,有着孕育“天子”的神秘传说。我曾三次徒步天子岭,登高西眺,湘江似一条玉带蜿蜒南来,江流两边平畴田野,村舍俨然。东岸建安司前身为零陵故郡,两千多年前的古邑司城依稀可辨。自建安司而下,凤凰嘴、大坪等渡口,作为红军抢渡湘江的要地,一度腥风血雨,其悲壮惨烈,惊天地,泣鬼神。这块鲜血浇灌的山川沃野,蕴含了太多传奇。 大坪:红军长征湘江第一渡 大坪渡口位于凤凰镇大坪村,距全州县城约30公里,西岸为绍水镇洛口村。渡口上游500米有咸水河、下游2.5公里有白沙河注入。
大坪渡口航拍图-马震宇摄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自赣粤湘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进到道县、江华、江永一带。11月25日下午5点,中央军委发布前出桂北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26日,中央红军右翼先锋红一军团二师的四、五、六团及一师二团(一师一、三团尚在道县配合五军团打击尾追之敌周浑元部)和军团机关经湘桂边界的永安关进到灌阳文市,直奔全州。此前,红军侦察科长刘忠率“先锋中的先锋”侦察部队潜入全州,发现这个历来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竟然是一座空城!原来早在20日,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致电蒋介石称红军进攻龙虎关,急需调全州兵力支援,所缺防务由湘军填补。蒋介石于22日复电同意桂军南移。这样,桂军迅速撤离,湘军迟迟未到,国民党精心布下的“铁三角”、“口袋阵”,在全州与界首的湘江防线就出现了百余里“真空”地带。 27日凌晨,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主力兵不血刃地从凤凰大坪渡过湘江。红二师四团走在最前面,过江后到绍水,迅疾沿桂黄公路南下,抢占了全州与兴安交界的湘江古渡界首;红六团负责控制界首以北至大坪的湘江沿岸所有具有重要价值的渡口和重要阻击阵地,第二天将界首渡口交给赶来的红三军团四师,为后续中央红军抢渡湘江打开生命通道作了坚实的铺垫;红五团奉命抢占全州城,但由于湘军刘建绪的前头部队先行一步占领县城,并在城外布置了警戒线,双方在离城4公里的鲁板桥发生遭遇战,红五团撤退到脚山铺,在军团部指挥下在桂黄公路两侧的山头上开始布置阻击阵地。同日18时,中央军委朱德给林、聂发电:“……军团之任务:1、保证一军团、军委与五军团之通过及在全州与界首之间渡过湘水。2、坚决打击由全州向南及西南前进之湘敌一路军……”28日,红一军团在脚山铺公路两边的山头构筑工事,从29日晨激战到30日晚,当晚退到白沙河一线,坚持到12月1日下午,坚决拦截妄图南下封锁江防的湘军,确保了渡江通道的畅通,也付出了伤亡6000人左右的代价。
大坪渡影视基地-伍祖华摄
红一军团为湘江战役中最早渡过湘江的部队,大坪渡口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第一渡,也是敌军封锁湘江的最后一天仍有红军抢渡的渡口。12月1日,军团政委聂荣臻发现其编制内的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没有过江,派出一支小分队,绕过敌军,在大坪上游带十五师渡过湘江,从黄沙、咸水经山口赶向部队。 1990年代,电影《长征》在这里开拍取景。21世纪以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我的长征》,广西电影制片厂大型专题片《长征从这里走过》,电视剧《长征》等都在这里开拍或取景。 今年初夏,我和几位朋友到大坪,走在青石板铺就的渡口石阶上,抚今追昔。1980年代中期,政府为解决两岸行路难问题,出资购买了一艘大铁船,可载汽车,容纳近100人;90年代中期,大铁船也不再适应,政府再次在渡口下边修建大桥。现在的大坪渡口,除了村妇浣衣、渔者泊舟,几近荒芜。 站在渡口边,眼前深水静流,水面烟气飘袅,往事鲜活又迷离。斜对岸影视基地上搭建的仿古民居,高翘的飞檐和马头墙,默念八十多年前那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凤凰嘴:牺牲红军最多的渡口 前年看文友马震宇的公号图文,湘江与它的支流建江的交汇处的形状恰似一只凤凰的尖嘴,两水间沙洲上的小村庄如凤凰的眼睛,这个“凤凰嘴”名副其实——湘江东岸的天子岭,则是一只硕大无朋的凤凰,正俯首濯缨。他感叹道;“我真佩服古人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他们没有可以升到空中俯瞰大地的工具,他们是如何命名这块土地的?”大地的造化和前贤的命名,真是神奇不已。
凤凰嘴航拍图-马震宇摄
“凤凰嘴”与湘江古渡相距不过一里,如今还是扯船过渡。渡口东岸的街巷曾是凤凰公社,为农副产品集散地。凤凰嘴上下游一带水流平缓,河床较宽,还有董家堰、八字堰、等堰坝,有些地方泥沙冲积,秋冬枯水期可徒涉过江。 1934年9月初,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从凤凰嘴涉渡,横穿桂黄公路,翻过越城岭到西延山区,北上湘西黔东,与贺龙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11月30日,正是湘江战役最趋白热化之际,桂、湘军阀南北夹击,急欲封锁湘江通道。而此时,由于中央和军委机关的两个纵队辎重缠身,行动迟缓,红军12个野战师中还有8个师未能实现全军在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原定计划,形势危急。脚山铺-白沙河、新圩-古岭头、光华铺-界首这三条保护湘江通道的阻击线压力越来越大,中央军委的多个电文开首都是“十万火急”、“万万火急”。11月30日凌晨3点,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联名给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下达了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分期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既是作战命令,又是思想动员和政治命令,战况已到千钧一发之际。红八军团原定跟随中央机关之后从界首浮桥过江,但那里水深流急,一旦浮桥被炸,在寒冬泅渡将变得异常艰难。为避免更大损失,12月1日凌晨1点30分,中革军委命所有江东部队到凤凰嘴上下游一带涉渡过江。当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红八军团先后急行军至凤凰嘴涉渡。
1日上午,九军团由石塘经铁炉头、余粮铺,过建江麻子渡(今麻市),穿柳山尾、左家坪,到凤凰嘴过江。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李雪山在回忆录《紧急渡湘江》中用了“凉气袭人”、“冰凉入骨”等字眼。对于红军来说,“冰凉入骨”不是问题,最大的危险是涉渡时遭到敌人的“半渡而击”和敌机的“低空轰炸”。 在1日下午赶到江边的红八军团属于最后一支渡江部队,损失特别惨重。八军团从石塘到凤凰,为了掩护五、九军团在杨梅山与桂军之追敌发生激战,后节节撤退,在凤凰嘴与建安司抢渡湘江,遭敌机狂轰滥炸,死伤无数。特别是尔后追来的桂军,在东岸用机枪扫射,红军纷纷倒在江中,鲜血把一江水都染红了。过江后的部队在李家村竹林里隐蔽时又遭敌机轰炸,死伤数百人。待翻过越城岭到西延(今资源),一万余人的八军团仅剩1200人,在贵州黎平缩编成一个团,编入五军团,八军团建制撤销。 硝烟之后,李家村等周边群众,在江边掩埋了三天烈士,而更多的则沉入江底。在下游的全州城北一个叫岳湾塘的江湾处,尽是顺流而来的红军战士尸体,宛如浮萍满江,其状惊心动魄。全州沿岸百姓不忍,遂有传谚:“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湘桂走廊上的全州,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都不乏征讨杀伐。从秦始皇溯流南征,到汉高祖刘邦击破淮南王英布,到唐末黄巢领军顺湘流北上中原,从南宋抵御蒙元到南明抗击满清,再到太平天国过境,战船长戟,刀光剑影,都在这里留下反反复复的杀戮,明明灭灭的印迹。最令人感喟的是,红军血战湘江的悲壮。中央有党史研究者说过,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严重、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90年的战争史上,乃至现代世界战争史上,其残酷性、惨烈性能够与之相比的,也屈指可数。” 毛主席诗云:“五岭逶迤腾细浪”。湘江战役这朵“细浪”,乃中共史海中的警醒之浪、血泪之花,是生死攸关的转捩,是扭转危局的子夜,为中央红军改湘入黔召开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埋设了伏笔。这一笔,浓血重彩,足以改变中国。 站在天子岭山脊,远眺湘江北去,逝者如斯,感怀凤凰涅槃,历史如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