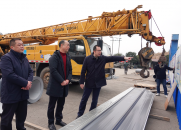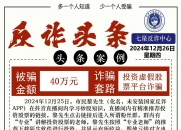|
山角驿,明代全州湘江段五大重要水驿之一,
始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至康熙二十九年改作巡检司,
又成为全州(西延除外)仅有的两个巡检司之一,是全州重要的官方机构,
存世长达数百年,黄沙渡与黄沙关的历史应比山角驿的历史更久远。
如此重要、历史久远的古渡、古关、驿站,
当今人们对其所处位置,知之者甚少,
偶有相关大作见于书报,对其位置也是模棱两可。
由此,今有必要对遗迹所处位置探究一下,以求究竟。
(山角驿、古黄沙度遗址)
一、从古籍记载中考证,古黄沙渡、山角驿、黄沙关、所处位置就在今黄沙河镇竹下村委下张家湾村湘江边。 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由永州知府虞自铭主修的《永州府志》载:“全州水驿四处(实为五处):洮阳驿(在州治右者,即广山驿之寓舍也)、柳浦驿、山角驿、城南驿(在州南一里广山)、建安驿”。明代正统全州志、成化全州志、嘉靖全州志均已佚,三处古迹如何记载无从查阅。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载“黄沙关,州东北七十五里(按:实五十五里,笔误),道出永州府,关下有黄沙渡,……旧皆有兵戍守”,他引用的《舆程记》载“又山角驿,旧在州东,洪武四年置,嘉靖六年移置于黄沙渡,或谓之洮阳驿”。康熙岁次己巳年(公元1689年)由黄志璋修纂的《全州志》载:“山角驿,在升乡,洪武四年建,嘉靖六年州守沈尚径移建黄沙河,今改巡司”,乾隆全州志对山角驿的记载照抄于康熙版全州志;民国二十四年《全县县志》油印本载:“山角司署,在黄沙河,距城五十里,现改为洮阳小学校”,又载:“黄沙关在升乡城东北六十里,道路出湖南永州,明加靖(按:应为嘉靖)六年,山角驿置此,清康熙二十七年,改巡司,清末废”。公元1637年中国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道“丁丑,闰四月初八日,夜雨霏霏,四山叆叇,昧爽放舟,西行三十里,午后,【分顾仆舟抵桂林,予同静闻】湘江南岸登涯,舟从北来,反曲而南,故岸在北。是为山角驿,地名黄沙。西南行,大松夹道,五里,黄沙铺(按:指今黄沙河东岸街)”。而现代一些作品中,也有对上述三古迹的相关描述,如著名作家朱千华老师《徐霞客广西足迹探秘——徐霞客踉跄入广西》中,将徐霞客上岸地点定位于今黄沙河渡口,广西师院黄权才老师《古诗所记录的广西驿站——广西历史文化之光二》中,将山角驿定位于车头村,还有其他许多相关名师大作中也有其内容,但对三古迹所处位置定位大同小异。 纵观上述古籍与作品,发现他们对山角驿所处位置的描述不尽相同,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黄沙关、黄沙渡、山角驿的描述,应是录用明朝旧志所载,康熙《全州志》对山角驿的描述也应是引用旧志,但相比《读史方舆纪要》,内容不如前者全面,且有所改动,将“黄沙渡”改成了“黄沙河”,在全州地域名中,“黄沙河”三字首次出现在官方所编古籍中。 “河”与“渡”,是一对紧紧相连的鸾生姐妹,有河必有渡,但就一字之差,造成今人对相距五里的两个“黄沙”之地的理解混乱,今之黄沙河东岸街,在乾隆《全州志》及之前旧志中,没见过“黄沙河”之称呼,均称之为黄沙铺、黄沙市、黄沙堡等,直至当今,黄沙河周边,凡说当地方言(土话)的村屯,对黄沙河的称呼均为“黄沙街里”、庙头一带操土话的村屯称呼其为“黄沙街头”,对黄沙河的称呼均不带“河”字,康熙《全州志》描述“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州守沈尚径移建黄沙河”,其中“黄沙河”应指的是“黄沙渡”,如果指的是今天之黄沙河,那么,徐霞客在110年之后的“丁丑”年(公元1637年),就不可能在黄沙铺下游五里的黄沙看到山角驿了,因此,康熙《全州志》所说的“黄沙河”与《舆程记》载“黄沙渡”是同一地点,即黄沙河就是黄沙渡、黄沙关,今黄沙河是沿用山角巡检司所在地古称——黄沙河而来的吧。搜遍全州现有志书,发现民国二十四年《全县县志》才开始将黄沙铺(市、堡)改称黄沙河,该志对山角驿(或山角巡检司)和黄沙关的描述自相矛盾,该志描述山角司署离县城五十里,而黄沙关在城东北六十里,变成相距10里路的不同地方,其中山角驿与县城距离比明代志书所载减少了5里,变成了山角驿与今黄沙河同在一处,但在“关隘”的描述中,山角驿又与黄沙关同在一处,且与县城的距离又变为五十五里,再搜看康熙全州志、乾隆全州志,整个清朝时期没有山角巡检司再迁移的记载,民国时期,全州县府也没有设立“巡检司署”这么个机构,民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将一个已作废了的旧机构搬来搬去。因此,将山角巡检司移到今黄沙河,然后“改为洮阳小学校”的说法依据不存在。但,也许清朝某个时期官府将山角巡检司移迁今黄沙河后,当朝志书或疏于记载或在黄沙本域内搬移不作记载了,这两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朱千华老师“黄沙河渡口登岸”之说,可能是只知今之黄沙河镇不知下还有古黄沙,将两个“黄沙”合成一个“黄沙”造成的吧,所以在其作品中,描写徐霞客登涯后的行程,“西南行五里,到黄沙铺”的行程没有了。黄显才老师的山角驿在车头村的说法,虽然大方位及遗址与县城间的距离正确,但把湘江东南岸与西岸搞反了,车头村在湘江西岸而非徐霞客所说“南岸登涯”,且西岸无涯可登,只有长达两公里的平缓的黄沙滩岸,只有黄沙渡的另一边渡口就在这黄沙滩上,或许“黄沙渡”之黄沙二字取于此长长的黄沙滩。徐霞客对黄沙及山角驿的描述最直观,他与《舆程记》描述的一致,细致准确,毕竟是他亲身经历的,不象旧志,在书房照搬前志,有时照搬还弄错。综上所述,古籍资料说明了山角驿、黄沙关所处位置就在今黄沙河镇东岸下游五里的黄沙渡,即下张家湾村旁之湘江边,其中的山角驿站清代是否迁移到今黄沙河镇有待进一步考证。
(徐霞客当年弃舟陆游全州登涯处)
二、从各自所处位置与县城距离来核实,古黄沙渡、山角驿、黄沙关遗址与张家湾村、印山重叠,它们在同一地点,而黄沙铺在它们上游五里处。 《读史方舆纪要》载“黄沙关,州东北七十五里(按:实五十五里,笔误)……关下有黄沙渡”,说明黄沙关与黄沙渡在同一地点; 康熙《全州志》记载的:“印山在县北六十里”、“山角巡检司在黄沙河,州北六十里”,说明山角驿与印山在同一地点。
“印山” 是明代县内有名风景山,在下张家湾村旁,渡口处在“印”的把柄位置;乾隆《全州志》载“黄沙渡,在城北五十五里”、“张家湾,离城五十五里”、而“黄沙堡(按:今黄沙河东岸街),离城五十里”,上述地点与县城的距离,虽然康熙全州志描述是六十里,而乾隆全州志描述的是五十五里,有所不同,但同一版本志书描述的“关”、“渡”、“山”、“村”始终都在同一地点。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距离描述不同,是不同时代对距离认知差异问题,这很正常。两版志书的描述与徐霞客描述的“湘江南岸登涯……,是为山角驿,地名黄沙,西南行,……五里,黄沙铺”也是一致的,说明张家湾村、黄沙关、山角驿、张家湾村同在一处,且与黄沙铺相距五里。 (东岸首事募化石碑) 三 、遗址实地考察、村民对遗址的称呼印证了这里确实是古黄沙关、黄沙渡、山角驿的遗址。
笔者老家就在印山脚下的黄沙河镇下张家湾村,为了察看遗址,前几日特意回老家一趟。因本人生于斯长于斯,对这一带地理环境是相当熟悉的,我时常在想,沈州守为什么会把山角驿移迁到此呢?山角驿在州城东存在了156年之久,是什么原因促使沈州守动了搬迁之念呢?从前面《永州府志》记载可以看出,五个水驿有三个在州治,柳铺驿至全州县城这段长达40多公里且最繁忙的水道,没有一个驿站,因此,水驿分布不均可能是搬迁的第一个原因;另一个就是当时这里的独特的地理位置,由于处在楚粤相交处,人员、货物流动大,与永州高峰乡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旧时在没有公路、铁路的情况下,永州地区南片官民,取道水路北上或南下,一般会从安道市(今恬美村附近),右拐至黄沙渡,此道无论在军政、民间运输上,都是一条从陆路到水路过程中最便捷的通道,也是连通全州正北陆路官道与东北陆路官道最便捷的通道,这或许就是山角驿移迁到此的第二个原因吧,登上印山岭峰,陆路正北大道、东北大道、湘江、渡口、驿站尽收眼底,出渡口上方印山岭与米珠山狭口有两条大道,向东:直通枣木铺至永州府;向西南:又通向黄沙铺,这狭口正是一个天然的隘口,难怪乎古人会把黄沙关设于此。今随着公路的出现、铁路的发展,古黄沙渡慢慢淡出了历史的角色,“黄沙渡”于民国初换成了“车头渡”(见民国《全县县志》),东岸埠头下移,西岸无固定埠头,渡船沙岸随处可靠,但此渡最终于1990年代末期被全州县人民政府取消。驿站遗址上现被厚厚的杂草覆盖,杂草下面时不时发现有拳头大小已经没有棱角的烧砖,地埂上有许多的瓦砾、残砖,听村民们说,前些年有人在地里挖出过许多烧砖,这显示古时这里曾有过大遍古建筑,老人们说的通向古黄沙渡的大青石板路早就没有了,1958年修灌江渠道时狭口古道挖掉了,1980年代修灌江渠道排灌站时码头全毁,我童年时看到的码头水边几块大青石现也不见了,听父辈说,走向码头石板路的左边,原有一溜七、八块大石碑,后陆续被村民抬走,用作房屋建材。现唯一见到的一块字迹有点模糊的《东岸首事募化芳名口口》碑,也被村民抬至一提水埠作埠石了,但也可以说明当年渡口管理人员存在过。渡口下游河湾被一堆堆挖砂抛弃的河卵石占据着,昔日宽阔的河湾变小了,徐霞客当年所登的石涯依然立在河湾北岸,徐弘祖说“故岸在北”,其实“涯”也在北,但今长满了荆棘野树,更难攀登了。自明洪武年间从江西迁住于此的我村村民,一直以来称此地名为“路站里”,路站与驿站意思差不多,今路站虽然没有了,但对此地的称呼一直还在沿用。由于“路站里”与当地土话“老宅里”音近,经过上百年的演变,许多人把此地当老宅子理解了,查资料,我村自江西迁来,从没到江边居住过,“老宅里”是音近而讹也。
随着江帆的渐渐隐去,汽车、火车、飞机成为当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驿站早已消失成为废墟;黄沙关上的刀光剑影、峰火硝烟已伴随着滔滔湘江之水北流而去,只有山头上依稀可见的战壕、炮坑显示着旧时曾经的严守和撕杀。岁月在流失,但历史不能被遗忘,山角驿作为明代广西水驿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对促进中原地区与全州乃至整个粤西地区的经贸往来、人员交往、信息传递所起的作用,我们不能将它堙没于历史的烟尘中。
|